目录
快速导航-
非虚构 | 心之翼
非虚构 | 心之翼
-
叙事 | 海獭11号
叙事 | 海獭11号
-
叙事 | 春回大地
叙事 | 春回大地
-
叙事 | 露从今夜白
叙事 | 露从今夜白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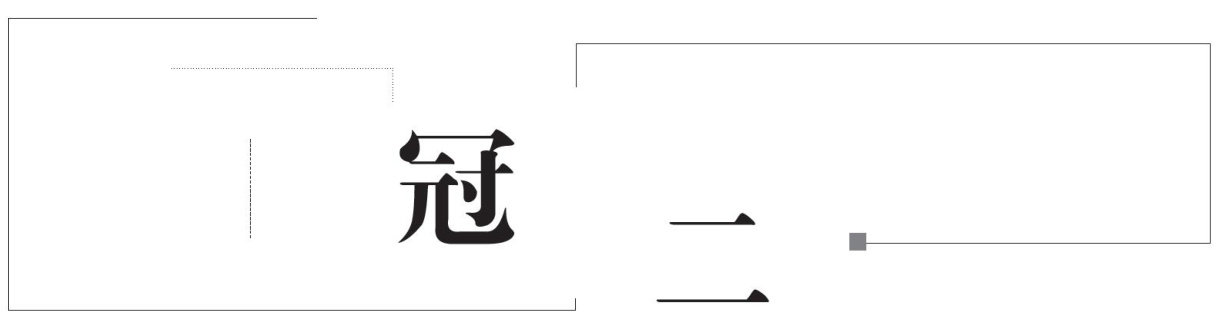
叙事 | 冠二
叙事 | 冠二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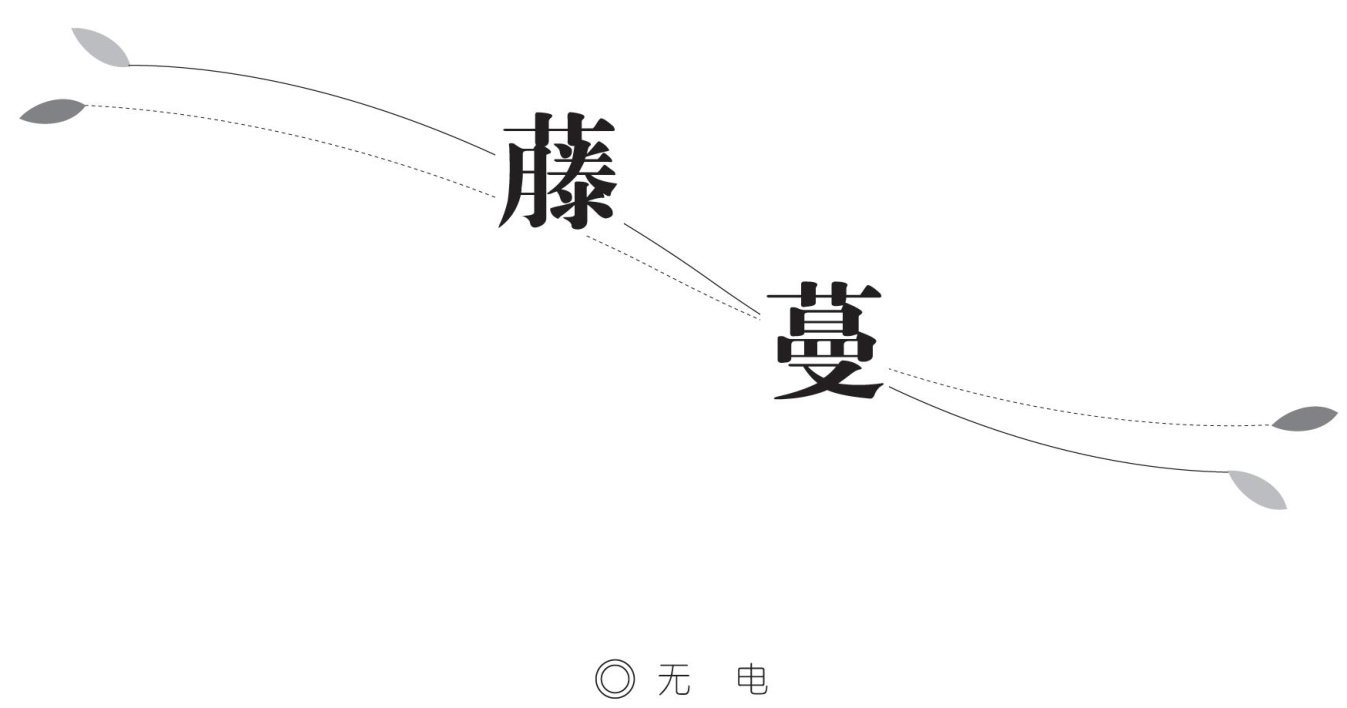
叙事 | 藤蔓
叙事 | 藤蔓
-
叙事 | 蝴蝶梦
叙事 | 蝴蝶梦
-
叙事 | 布朗运动
叙事 | 布朗运动
-

叙事 | 坠落之后
叙事 | 坠落之后
-
叙事 | 九重盘古山
叙事 | 九重盘古山
-
散笔 | 终非岩间客
散笔 | 终非岩间客
-

散笔 | 墨痕
散笔 | 墨痕
-
海国志 | 尼泊尔行记
海国志 | 尼泊尔行记
-
新乡土 | 孤影长
新乡土 | 孤影长
-
新乡土 | 唤水记
新乡土 | 唤水记
-

新乡土 | 云上茶园
新乡土 | 云上茶园
-
吟咏 | 历史
吟咏 | 历史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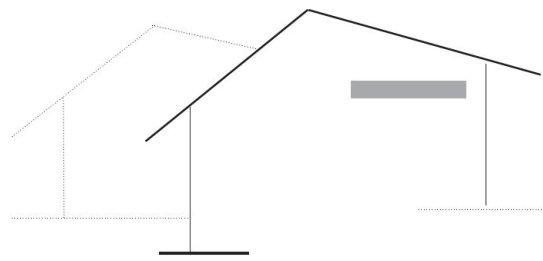
吟咏 | 长子
吟咏 | 长子
-
知见 | 偶然是最伟大的小说家
知见 | 偶然是最伟大的小说家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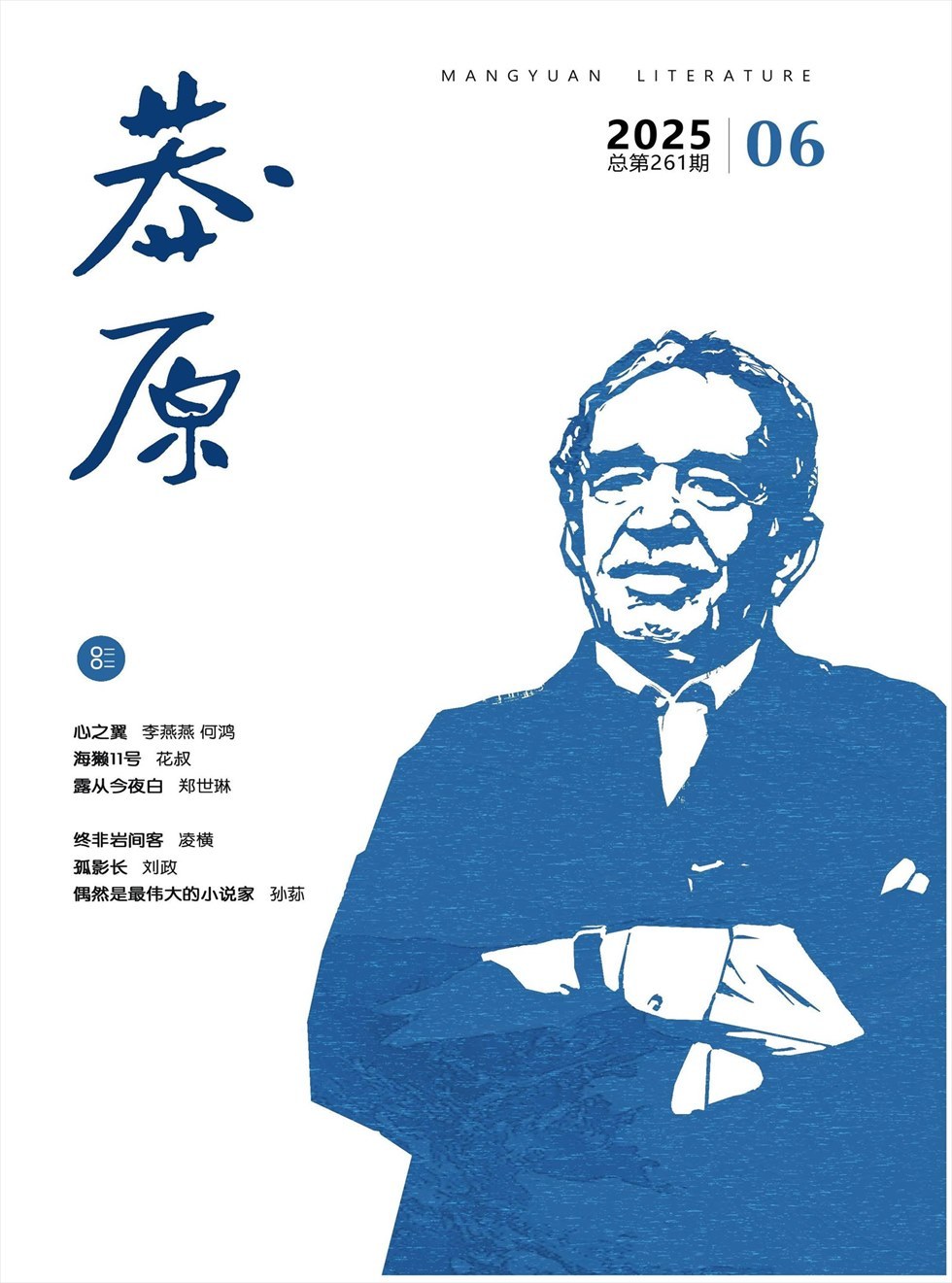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 登录
登录